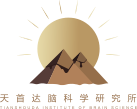自闭症儿童回归日记(二)
今天早上想起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自闭症的治疗原本选择在了杭州野生动物园旁边,昨天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就选择在杭州市区八卦田景区那里进行的,今天又转回到野生动物园旁边,我突然想到这可能是一个天意的安排,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自闭症的儿童去上这种行为康复辅导课还不如直接在野生动物园里面玩,而且在动物园旁边住宿也比较便宜,同时这个野生动物对于小朋友应该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有的自闭症儿童在中国人来看叫神不足,如果用西方的现代人理解的词语,我只能用神经系统的全面能力削弱或者指标严重低下,他无论是神经的通路还是神经的这个量都严重的不足,那么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对人类社会的一切就更加没有能力和不愿意参与,但他对于所有非人类的这些原来本来具有的东西是很开心的,所以说与其花很多时间带他们去上康复课,还不如带他们去逛动物园,应该这个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昨天治疗的一个自闭症儿童的家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科学家。当然他自己首先是个很优秀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看了非常多的书,人生也很成功,但是让他视野更开阔的原因是因为他小孩的生病,他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开始,自己去学习医学、学习生物学,去寻找更多的方法,这个过程中他开阔了,他就不再像原来那样固定的思维,他找到我们并觉得他的孩子有很大的希望能治好,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他相信他的孩子能治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自闭症儿童、自闭症儿童的家庭和整个治疗自闭症儿童的医疗人员99.99%的人认为自闭症是治不好的,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治不好,所以治不好。从来没有想过能干好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干好呢?这种主观的假设和全社会的集体认定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根本不可能治好。最终一个治不好的自闭症儿童给这个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
首先,自闭症儿童直接的治疗成本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价的成本。第二个是他对家庭的消耗。基本上自闭症儿童家庭的一到两个成员的精力和青春就完全的放到照顾和监护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身上,而且很多自闭症的儿童带有自残的行为,所以监护人时刻都不能离开。这种消耗和这种巨大的牺牲可能就源于一种无知,如果你有愿力有希望,同时寻找合适的方法,可能一半的自闭症儿童都是可以治愈的,他们可以像健康的孩子一样去上学读书,去享受教育,去快乐的生活,去谈恋爱去抚养孩子......他们完全可以拥有正常人拥有的一切,而且可能比其他的孩子做的还好。但是很可惜,这一切就在他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个集体的诅咒给定格在那里了,所以说思维的局限是最大的局限,那么如何走出这个误区,走出这个思维的局限?我想这可能需要全社会思维的改变,全社会一个更大的爱心,一个社会层面的、全世界层面的和全人类层面的一个爱心。
如果我们大家都想自病症能治愈,都想走出这个困境,这个社会是可以走出去的,相较于100年前的那个社会,我们现在的社会缺少了更多的动力、活力和爱心。
原来美国好莱坞有部大片叫《泰坦尼克号》,那个片子拍得怎么样我不评价,因为已经得了奥斯卡奖。那个片子的后面其实有更多的那种人性的崇高的东西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我在美国哈佛访学的时候见过一个跟这个相关历史记录,其中有一个人的妈妈为了纪念他的孩子就建立一个游泳馆,好像在哈佛里面有规定所有的学生是必须要学游泳课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孩子的原因,其实那一次沉船事件许多人表现出了非常崇高的人性。那里面核心的背景是什么呢?是这些人因为他们拥有比较高的神智,这种神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是他对自己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一种认同。
我还想到那个时代很多基督教的牧师去其他相对贫困的地区去传教,就为了一个信念,可以把几十年自己的一生都贡献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人精神生活和品格的高尚,对自己精神上的要求有多高,这样的事例已经有很多,在中国的云南,中国一些边边角角的角落里有很多这样的小教堂,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迹。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在忙着应付各种各样的生活,房贷、车贷,然后有这么多贷款压力的情况下,怎么把它换成一个更好的房子,承担更多的房贷,怎么去换一个更好的车子。我不知道我们都在干什么,但是你干的事情其实是很无聊。物质生活是看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其实没有改变任何那个车的原理,那个车还是四个轮子还是一个方向盘,之所以说你干的事情是很无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贴了一个更高的品牌,那无非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行为。
车到飞机,轮船是一个变化,但车在品牌之间变换,这个不算变化。
最近因为治疗的原因,我们接触了现在很多治疗自闭症的医疗方法和手段以及过去几十年大家所做的那些工作,应该说自闭症是随着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而出现的一个病症。最早是从美国开始,美国的发病人数比较多,现在大概六七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这个如果平均到孩子身上的话,这个数目就相当高了。在美国生活的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在美国自闭症患者非常之多,多得难以想象。
中国现在公布的数据是一千万,这个数字相对于我们总的人口基数来看现在还不是太多,但是增长率是非常吓人的,估计最后也会到像美国一样的患病比率。薛史地夫教授在美国研究这方面研究了很多年,他给的数字是一个自闭症儿童直接的经济损失大概是一百万美金,我不知道是治疗的费用还是直接的社会成本,这里面还没有包括照顾孩子的付出,这个成本其实社会是负担不了的,虽然美国人比较有钱,但是那也是5万亿美金的财政支出。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这个情况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案。
我个人看了这么多资料以后觉得首先过去的治疗人员,尤其是参与进来的医护人员其实他们是非常有爱心,他们奉献了很多。这个不是简单的言语能说清楚的,因为没有接触过自闭症治疗的人不清楚,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孩子的时候,你需要非常大的耐心和爱心。因为孩子安静不下来,你要接受他并且可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只能做一点点事情,你必须跟他在同样一个能力和频率上,所以这一点会让很多人很崩溃,因为现在社会大家生活节奏太快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治疗过程更优化从而提高效率。
首先,现在对于自闭症的标准都是人为的在一些问题和指标上去套,给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和答案。这种问卷式的其实是非常粗糙的一种方式。这个对自闭症的认定、界定和治疗界其实是非常不谨慎的,对于真正治疗和和家庭的防护使用上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这一点可能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标准,否则的话在使用过程中非常的不方便,而且没有可操作性。第二点就是现有的方式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方式。
现在自闭症的治疗是带着孩子去强化、去训练,怎么去和怎么样去参与到我们现有的正常人的社会活动中来。其实这样非常的不好,因为你的出发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如果我们真正关注孩子,关注他的健康,首先应该关注让他好起来应该是站在他的角度为中心的,在他的标准上让他慢慢成长起来,而我们现在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让他或者让他们怎么跟得上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为的对孩子不尊重和傲慢且粗糙的念头在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需要很大的改变。
首先我们设定的方向是一个远大的方向,怎么样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一个更优秀的孩子。第二个我们所在的角度应该是怎么样把自己降格到孩子现在的水平上的这么一个更精微的角度。
你如果想治好一个自闭症儿童,你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自闭症儿童,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的行为是什么意思。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去治疗,你都不理解他,你怎么能治好他呢?所以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想我们在治疗每一个孩子的时候,首先你先变成和他同样的心理状态,同样的精神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你就知道应该往哪里走,因为你跟他是在同一个频率,治疗也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同时当你又下到一个更低的标准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走回来,你知道怎么走回来你就把他带回来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能也不太关注气质了,大家现在就只关注外形。但是确实呢,气质是一个既存在而你又能感觉得到的这样一个东西。
来我们这里治疗自闭症的孩子的妈妈在治疗过程中经常都是说,哎呀,我觉得这些孩子现在变得特别漂亮,而且越来越漂亮了。这个可能说用“气质变化”更贴切。
每当这个时候其实我脑袋里总在跳出一首儿歌,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叫“我们都是木头人儿,谁也不许动一下...”。几乎那个年代的小朋友都玩过这个游戏,就特别想跳出来说一句话“我们都是自闭症,我们一起去沉默”。
包括世界五大宗教,大家都在暗示一件事:就说人都是从神变过来的。可能我们地球上的人都是天神被贬到了地球,那这个过程呢,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慢慢的大家就都在遗忘,都在自我的闭塞,慢慢变得越来越自闭,这是一个减少觉知的过程。
人也是一个动态的这么一种生物,可能在上古和远古的时候人是拥有更接近于神的那些能力。所以那个时代神和人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优越感,越往后这个变化就越大,到两千几百年前的时候,包括古希腊的很多神话都是讲人跟神互相互动,那中国古代的很多神话里也讲得非常多,人神共居。
但是慢慢随着人的这个执着的增加,自我意识增加、欲望的增加和觉知的减少。觉知能力在降低,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现代人。
天景生公益基金会在成立的时候我就总在讲一句话,“我们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拯救自己”。
很多人都以为付出了非常的多,其实呢越多的付出,可能在无形当中又有了很多这些过程带来的回报,这些回报其实是不期而遇的。我们在帮助这些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警醒了自己,更多地发现了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或者说有很多惊喜的变化是在孩子和我们自身同时在发生的。我真的没有认为我们在治疗这些孩子,其实是我们跟这些孩子一起在成长。